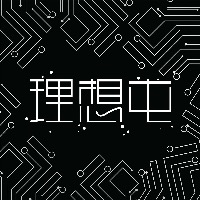大家好,我是翊瑄Camellia,朋友们都喜欢叫我小球或者球姐。 我曾在新西兰生活十年,又在伦敦待了两年,如今常驻葡萄牙,一边翻译,一边写作,一边远程工作。 每月更新 3-4 篇内容,灵感来自书本、旅程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「不确定感」。 这里可以读到数字游民的真实生活、语言背后的思想结构、用写作进行自我建构和灵性觉醒的内容。 我的网站:https://www.camelliayang.com/ 购买成功后,可加入读者群。
浅谈高能行动力的九个心法和人生转变十律
做了100个AI视频后,我开始思考:谁才是真正的创作者?
Sora2无疑是这周最热门的话题。到处都有人在讨论OpenAI这款最新的AI视频......
浅谈丹布朗新书、自我意识和增长智慧
上周,我有幸前往德国汉堡,参与了汉堡文学节,现场听丹·布朗(Dan Brown)......
大卫·森拉|用历史的杠杆,点燃创作者的火焰
在这个被效率、算......
南欧生活教会我的事儿
我常常想,如果命运的地图是一块岩层,那么我的人生就是不断从一层层压抑的沉积中钻出来。出生在山东,我的DNA里带着一种深重的业力:那种"要努力"、......
彼得·普特南的未竟之梦 | 关于科学、意识、神话与人类未来的故事
浅谈副业、AI受限、法拉利、米其林和克里斯蒂安·贝尔
简单编译下Poolsuite创始人Marty Bell的最新一篇博文《副业,是让......
时光切片|一周杂谈
过惯了数字游民的生活,常年漂泊不定,住处换了又换,行李越收越少,逐渐练就了极简主义的本领:不多买、不囤货,能带得动的才叫「我的」。
只有真正经历过在欧洲老式洋房里一层层......
和凯文·凯利相处的一天,提醒了我什么是“成功”
凯文·凯利之所以被人记住,并不是因为某项“惊天动地的大事”,也不是因为他渴望出名。事实上,他从不追求那种头条式的荣耀。和许多广为人知的企......
Ryan Holiday|斯多葛哲学流派(Stoicism)践行者【3】
美国知名畅销书作家、思想家和公关专家瑞安·霍利戴(Ryan Holiday)是我的一大榜样,之前小报童写过他的两期专题(第一部,第二部),本期再来分享一下我近期编译总结的他的另外几篇文章。